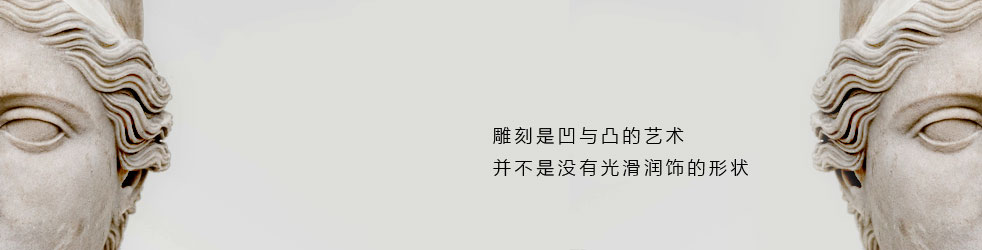
孙闯
大足县宝顶山大佛湾的《牧牛道场》摩崖石刻,因为直接描写社会生活,而为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多侧面的探索天地,笔者本文主要就雕塑本身的一些艺术处理及由此引出的相关问题谈谈一管之见。 如果从艺术评沦的角度来看一件作品,首先则要看它创作的初衷及表现出来的实际效果。《牧牛道场》由“未牧”、“初调”、“受制”、“回首”、“驯伏”、“无碍”、“任运”、“相忘”、“独照”、“双忘”等十个连续的情节组成,它借驯牛过程表现修行者通过不断“调服心意”被驯服而最后皈依的演变历程。本意当然是出于佛教教化的目的。但如果不看文字的话,展现在观者面前的雕塑简直就是乡村牧人的现实生活写照,通过观看一群小小的牧人驯服了比他们体形与力量大得多的牛,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劳动的智慧和力量。以至于被当地老百姓喜爱并呼为“放牛坪”。 好一个“放牛坪”!观看整个作品构图与布局,场面宏大,在长27米,高5米的岩壁中,这组雕塑的主体:十牧人、十头牛因势穿插在曲折蜿蜒的牧场背景中,他们年龄、衣饰各不相同,走坐卧靠动作姿态更是多种多样,在云雾缭绕场景中,还穿插有一些飞禽走兽而更显得生机盎然,它宛如一首浪漫的田园牧歌,而散发出逼人的世俗气息。 为什么在密宗道场中会出现表现世俗生活的雕塑?笔者认为外来的佛教雕塑到了宋代,除了题材来自佛经外,艺术上已全然是民族艺术的形式了,世俗化的倾向更加强烈。同时,程朱理学和儒、释、道思想大合流,文人画的思潮也进一步冲击着宗教艺术的统一天下,禅宗为了更好地宣传教义,把生活中具体、普通的日常活动都与习禅悟道联系起来,所谓“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连佛教本身也出现世俗化倾向,这就使它神圣的气氛更加谈化。在这时期雕塑所表现的内容也有很多曲折乃至直接地表现现世人生的题材,如表现仕女的形象——观音较之以前空前地增多,一批动摇人们固有的佛教意识,着眼于实际生活,并把虔诚的膜拜转化为享受艺术的情趣之作也应运而生,而世俗化的出现,又给予了佛教艺术的创造以坚实的基础,广阔的空间和发展的生机,大足宝顶大佛湾石刻艺术正是这期间的产物,因此,在密宗道场的经变故事中出现“放牛坪”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以放牛来比喻“禅宗”的修炼过程[注1],既然没有以前造像模式的约束,则雕塑家们当然可以相对放开手脚,按现实生活中牧人形象自由地塑造。他们本来就是来自土地,牧人与牛对他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形象,但他们塑造形象时也并没有完全照搬生活真实,而是把脑海中经过反复筛选过的沉淀形象、或者说经过形象思维加工过的能够驯服犟牛的牧人的容貌与个性,自由驾驭创造在石崖上。应该说,这时占主导地位的雕塑观念,已是融汇中外雕塑以后而形成的民族审美习惯、布局结构及制作经验。这也是我们现在观赏这组雕塑中仍可强烈感受到的迥异于其它宗教雕塑的那股堂堂正正的民族的主人气派的原因。 虽然,古代雕塑家没有给我们留下完整系统的雕塑理论,但我们观看先辈留下的大量雕塑,仍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他们以斧凿塑刀为笔,书写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辉煌历史篇章。观看《牧牛道场》这件技法异常成熟的作品,我们可以窥见作者对神韵的追求以及呈现的形神兼备的刻划。人物形象看似拙笨,然而仔细审视却非常传神,“驯伏”与“无碍”两个情节,合刻为一,二牧人并肩拥坐在山坡上,前牧人向后面的牧人诉说着什么,引起后者开怀大笑,两条牛中前面那条似乎也在通情地倾听主人的述说。塑造者在这里紧抓牧人瞬间最富神韵的动作,以简明、夸张的手法,突出地表现了牧人的姿态笑貌与情感,而不拘泥繁绣细节的真实,他们重点着意刻划的是牧人的精神与神态,而不是解剖形的表面正确,如果要问两个牧人在说什么有趣的事?我们不知道,也说不清楚,但他们仿佛忘掉一切的高兴劲却又能被我们强烈地感觉到。 在“双忘”这组雕塑中,那个以苍天为屋,大地为席,袒胸露腹仰身酣睡的牧人与从树上爬下来的那只顽皮小猴的组合,既表现了一个襟怀坦荡的主体人物,同时也很巧妙地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构思构图不能不叫人掌称绝。 我们如果从雕塑所呈现的人物形体来审视这件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对人体的处理下过相当的苦心,尽管雕塑形象经过夸张,甚或概括,但就其在空间的分割来分析,他们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以传统的意象艺术造型观来自由地把握与运用人体比例,并让人体结构的表现严格服从思想感情的表达,他们首先关心的仍是表现对象的内在情感及由此派出生来的神态和创作者主观意图的统一。分析那个仰睡的牧人,从比例上来看,盆骨以下显然作了极大幅度的调整,大小腿每段只有一个头长,乍看头大,身躯长腿又太短,但整体看又显得非常协调、饱满。胸部的处理、腹部的刻划,既注重解剖的合理,又不过分强调解剖结构的低点,而是处理得概括丰满,用雕塑专业的眼光看,这种强调大体积与厚实的处理,使形体处于“放光”状态,不至于因光线角度的变化而使形有过度的阴影而发碎、变瘪。再看头部处理,虽然雕塑家们并没有按解剖详细地刻划颧骨、上唇方肌、眉弓等具体解剖形,但整体把握的头部却抓住了大轮廊、大特征,并作了高度概括,重要结构都处理得很到位,在此基础上再把刻划的重点放在五官眉眼部分的关系上,即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之中”。 在这组雕塑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关键部位,即艺术家想以体积的表现来引起人们注意的地方,仍是采用“弧线”的架构法则,以求最大限度地放足体积,并在其中运用方圆结合的手法造形。“方”使形体结实,“圆”又充满了生命活力。由于《牧牛道场》采用摩崖石刻这种艺术形式表现主题,如何利用崖势的问题自然也就摆在创作者面前,用好了则作品增色,用不好既费工,又生硬。观其作品可以看到作者解决这个问题是很成功的,作品中主体圆雕高浮雕与作为背景的浮雕过渡非常自然,并无突兀之感。岩间自然流水也成了雕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股从远古而流至今天的活水,使得静止的作品具有某种超越时空的永恒意味。 值得玩味的是,与《牧牛道场》相对北崖所刻的那个著名的“吹筚篥女”与这边唱歌吹笛的牧人遥相呼应,似乎你唱我和,共同吹奏着田原牧歌,其情其景充满诗意,使人心旷神怡。如果联系起来看,则两件作品的虚空间都扩大了几十米。从“吹筚篥女”所刻的位置上看,她与《六师外道,谤佛不孝》在整体上的关系,联系并不紧密,似乎拿掉她该作品更完整,但她与几十米以外的“放牛坪”反而其情相融,其境相谐,如果不是巧合,则笔者颇疑这是在雕塑没建之前,整体上已经作了这样的安排。至于穿插在雕刻作品中的动物则更使作品增加了很多情与趣:老虎凶猛无比,小猴活泼顽皮,那群牛的各种动态更是多种多样,这使人不能不佩服作者对生活的熟悉与把握动物形象上的准确。 在佛教雕塑中,造像多是以站、坐等静态为主[注2],但这组雕塑中的“受制”、“回首”却是用人的运动来表达内容,特别是在“回首”中的牧人,展现给观众的是个背面的人,全靠形体对比、转折、变化来形成韵律而传达主题,虽然他的动作与汉代“说书俑”相比没有那样大,但在当时已经是个创造了,因为长期的宗教雕塑,受仪轨限制,佛与观音都避免使用动作造型时,即使护法神王动作较大,但已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而《牧牛道场》的造像则很少程式的因素,造型生动、自然,其动作塑造具有作者很强烈的情感因素。这也是本文前面已经提到的原因,因为作者本身就是扎根在生养他们的土地上,直接从生活中提取造型元素的结果。虽然他们虔诚地刻划经变故事,但因为倾注了真实的感情和源自生活的真切体验,所以使牧人们就再不是一个个徒具美丽外表的躯壳的组合,而是真实、生动、具有活力的生命。 注释: 注1:胡良学《也谈“牧牛道场”》的宗派问题,《四川文物》1999年6期 注2:《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 1982年 (原载《当代美术家》1999年第1期 总第16期)
发表评论
请登录